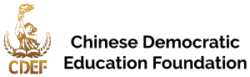以歷史文化為鑑的孫國棟、何冰姿夫婦
作者:余健文

孫國棟先生是著名歷史學家,一九二二年出生於廣州市,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四九年大陸變色後,孫先生與夫人何冰姿女士流亡至香港,於新亞研究所師從錢穆先生治國史,為新亞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孫先生歷任新亞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新亞書院文學院院長、新亞研究所所長,為唐宋史大家。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孫國棟先生就讀於重慶國立政治大学三年级,為響應國民政府「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毅然投筆從戎,參加「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加入青年軍二零一師,其後奉調到缅甸戰場,服役於新一軍孫立人將軍麾下。後被選拔為孫將軍撰寫參觀歐洲戰場的回憶錄。後因日本投降,新一軍奉命接收廣州市而未能成文。抗戰勝利後,孫先生退伍回南京復學,畢業後隨即回廣州市,於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與何冰姿女士舉行婚禮。孫先生後來回憶說:「十萬知識青年從軍運動」是我國偉大的抗日戰爭中動人心弦的一幕…… 寓有我民族艱苦奮鬥以雪百年國耻的痕迹。我能参加青年軍,實覺無負此生,足以自壮。」
四九年大陸變色,孫國棟先生與何冰姿女士流亡至香港,生活非常艱苦。孫先生先在香港私立嶺東中學工作,後因投稿「人生雜誌」為《人生》的創辦人王道先生賞識,並獲邀擔任《人生雜誌》的編輯工作。後又任《中南日報》主筆之職。
《人生雜誌》是王道先生夫婦為了追求理想而艱苦創辦的刊物,其作者多為當時流亡港台的學者。孫先生亦因《人生》的關係而認識了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名家,更因此而激發其以學術為終生志業之心。其時錢穆、唐君毅與張丕介先生眼見山河破碎,國土陷於馬列共黨之手,中國文化被摧殘殆盡,此為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千年未有的大災難,他們於是以傳承中國文化為其志業,在香港創立新亞書院與新亞研究所。孫先生於一九五五年考入新亞研究所,並辭退了研究所以外的一切工作﹐專心致力於學術。
孫先生回憶他選擇隨錢穆先生治歷史之因緣時說:
「研究所開學的第一天第一課,錢師問我讀過那些學術性的中國書。我把我讀過的學術性中國書列單報告他。他看了說:「先細讀我著的《國史大綱》罷。」第三天上第二課,錢師問我:「《國史大綱》讀了多少?」我說讀了一百多頁。錢師的面色已不大好。他又問我:「有些甚麼意見?」我說了幾點小意見。他說:「你完全未領會《國史大綱》的作意。你為甚麼兩天只看百餘頁?」我說因為最近很忙。錢師發怒說:「現代的學生,躲懶讀書,常用最近很忙為藉口,朱子說:做學問要有救火、追亡般逼切的心情,排百事而為之,然後才可以有成,那裡能夠閒閒散散地讀書。我這研究所是要找些能獻身於學術的青年,你既已願獻身於學術,那裡能因些俗務而荒學業。」我被申斥得汗流浹背。」
也是由於此一番的申斥,使他覺得「像錢師這樣老師﹐實在難得。」並因此決定拜入錢先生之門修歷史。當年的新亞書院與研究所是中國文化的重鎮,集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牟潤孫等國學、史學與哲學眾大師於一堂,非一般大學研究院可比擬。其教學形式亦不同於一般大學,它彷效宋明書院師友相勉之講學方式,老師與學生的關係尤為密切。孫先生於新亞研究所畢業後,即在新亞書院講授歷史。
孫先生數十年來在香港從事歷史教學,現今在香港大專院校的中文、歷史、及哲學系任教的教授很多曾受過孫先生的教誨。教學以外,孫先生更致力於唐宋史的研究,為學術界公認的唐宋史大家,學術著作豐碩,其對於唐宋社會門弟之變遷、唐宋之政制與官制之研究尤為史學界推祟。
孫先生於一九八三年從中文大學退休,移居美國舊金山灣區。孫先生退休後對歷史之研究從未間斷,學術研究之餘,他更撰文改正時論對中國文化的誤解。指出今日反對中共的仁人志士,每每將中共之專制獨裁歸罪於中國的歷史文化,以為中國人應絕棄自己所有而全盤西化,這是因為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真切的認識。蓋人如不能以自身的歷史文化貞定自己,以立其本,則亦絕不真能吸收學習別人文化的長處。此外孫先生並於《星島日報》、《星島晚報》、《世界日報》等報張發表大量的時論文章,以中國歷史文化為鑑,宣揚民主政治,批判專制政權。

新亞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合影(左起)柯榮欣、孫國棟、羅球慶、余秉權、唐端正。
八九民運期間,孫先生與夫人積極參與海外的支緩活動。「六四屠殺」發生後,孫先生為文寫道:「他們(北京學子)以青春之年而赴死,固然可憫;然而生命的價值,原不問久暫,與其卑微猥瑣而苟且偷生,何如充實光輝、軒昂磊落而赴死!」並為之贊曰:「凜凜千古,烈烈英魂,大哉生命,取義成仁!」「六四」以後,海外華人社區有不少人自覺對中國認識不足,時常邀請孫先生講授中國歷史文化。八九至九五年間孫先生曾定期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為香港學生作文化講座,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傳播工作,深受青年學子歡迎。
孫國棟先生於「新亞」求學與工作近三十年,既受「新亞精神」之薰陶,又與「新亞」先賢共同鑄造與深化了此一精神。在他身上具體表現出儒者之仁義並舉、剛建不息之性格。面對自己文化之不足處,孫先生與「新亞」先賢們皆採取一種理性的態度,他們以同情之心正面的去了解認識到中國文化之內部要求,籍此吸收西方文化之精粹,真正開出中西文化會通之正道。其目的正是要將民主人權與科學理性等普世之價值,吸納於中國文化之根本處,擴大貞定吾民族未來之理想,重建中華民族生命之常道。
「六四」以後,孫先生與夫人參悼念「六四」與促進中國民主的活動從未間斷,孫先生更長期為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擔任評審委員。
* **
孫夫人何冰姿女士是中國廣東省三水縣人,生於民國十三年(1924)九月十三日,終於民國九十三年(2004)二月十一日。何女士生於教育世家,其家族是民國初年推行新式教育的先鋒。她的外祖父參與創辦當時南中國最有名的學校─廣雅書院,此學校後改名為「省一中」。
何女士青年時代己協助母親沈芷芳女士在粵北自由區辦流亡學校,在抗戰極艱難環境下維持此流亡學校,一直到抗戰勝利。抗戰勝利後何女士畢業於中山大學,並與孫國棟先生結合。沈校長後來先後擔任廣東女中及女子師範學校校長,何女士亦任教於女師與女中以協助母親辦學。
中共戰火南移,廣州不能安居了,孫先生與何女士遷移到澳門。時孫先生失業,何女士每天早晨賣報和送早餐以 維持一家生計。四九年大陸陷共,何女士與孫先生流亡至香港,先在沙田信義學校任教職,後來改任校長十年。何女士對教育工作的盡責深為學生與家長肯定。一九八一年香港政府要拆卸信義學校,數百名學生家長請願的保校,最後得到成功,是香港百年來的第一次。可見學生家長對何校長愛戴之誠。
何女士於1981年退休移民美國,來美之後,即致力於詩經及爾雅釋草釋木的研究,又從事於文字學,她認為中華民族延續幾千年,中國文化必有不可磨滅的價值,而文化的基礎在文字,所以運用文字非常重要,而目前海內外的中國人,大多對中國文字甚少注意,尤其是自簡體字流行以後,文字變成一種純粹的工具,其文化涵義,愈發流失。蓋中國文化有其獨特之性格,它以中國文字為載體,故不能離開中國文字來理解中國文化之真精神。歷史上中國文字固然不斷在簡化,但這一簡化之過程亦是依隨文化之變遷而自然而至,非以政治行政權力強行為之。中共之本質是反文化的,它當初強行簡化正體中文字的目的,是作為中文拉丁化的過渡,而非今人之所謂普及文化。故中共五十年來推行的「簡體字」,實是摧毀中國文化之行為。由此觀之,通過「簡體字」以理解中國文化,只知文化之工具意義,而不能知文化之精神內蘊。何女士認為文字固應簡化,但必須合理地簡化,不應隨便亂簡。中國字有形、有音、有義,所以必須在不違背「形」「義」的原則下而簡。於是她又致力於採用淺易而有趣的方法解釋字義,並收集編理通用流行的詞語,俾青年人易學易用,為中國文化墊一點基礎。
何女士多方面的才華更表現在工藝上。凡有關中國文化的各種藝文,如書法、繪畫、篆刻、紡織、陶瓷、石刻、銅鑄、剪紙、金屬工藝等無不愛好,而且都有相當造詣。 她的陶藝作品常寓深意,或為受苦難者鳴冤,或為窮人吐露心聲,或描寫極權政府下人民生活的痛苦,或表現人生之艱難,或流露家園之思,或寫人性的複雜,或表露對「自由」之嚮往。她的退休生活,可謂多姿多彩。
在文字學研究與工藝創作以外,何女士更關心世局,時時以國家民族為念,痛恨專制極權,深盼中國能出現優質的民主政治,俾國人得享人權之褔,所以對於有助於中國民主運動的活動,都熱情參與,並常於公共場合為受苦難的國人發言,痛斥中共蹂躪人權的暴政,因其情感真摰,每次都使聽眾感動,熱烈鼓掌。
與孫夫人接觸過的人,都會感到一種溫馨而舒暢的感覺。她是一個獨特的生命,其獨特處在於她有一片赤子之心,愛憎分明,並時時表現出活潑的生機。其所以給人一種舒暢從容之感,則在於其真誠坦惻之情,無論是初相識或老朋友,她都以誠相待,不作無聊的應酬,不作隨便的敷衍。孫夫人的生命是一個至誠的生命,她獨能真實化中庸之所言之「誠」。故她處處表現出擇善固執之情。對於民主理想之堅持,對於自由之追求,對於專制政權的厭惡,終生未有改變。每言及中共摧毀中國文化與壓制人民的種種惡行,其悲憤之情,溢於言表。更常會拍案而起,謂要消滅暴政,必須使用非常之手段,甚至訴諸於暴力革命,亦不為過。有人以為她的言論過於偏激,不切實際,不夠客觀持平。但這正恰恰表現了她至誠生命的本質。她不以現實表面的是非為是非,不以實然之事亂當然之理,事事能以人文社會當然之義以衡量批判現實之惡。此正是她能擇善而固執之所至。